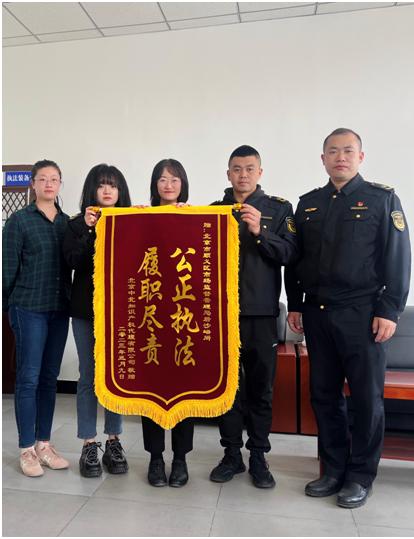2018年商标評審案件行政訴訟情況彙總分析(二)
應訴複議處
根據2018年第1期《評審法務通訊》中的數據分析可知,評審部門因商标法第13條和第44.1條原因而敗訴的案件比例出現了明顯增長(cháng)。通過(guò)對(duì)上述敗訴案件的詳細梳理,我們發(fā)現盡管多數案件是因事(shì)實認定分歧導緻的敗訴,其中不乏當事(shì)人提交新證據等原因所緻,但在部分敗訴案件中所展現出的法律适用路徑和态度尤其值得商榷。
一、關于第44.1條“其他不正當手段取得注冊”與其他實體條款并用的問題
根據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發(fā)布的《商标授權确權行政案件審理指南》17.5的規定,在不予注冊複審、無效宣告案件中,如果能(néng)夠适用商标法其他條款對(duì)訴争商标不予注冊或宣告無效的,不再适用商标法第44條第1款。從該規定表述來看,似乎其他實體條款在适用上存在優先性,在其他條款成(chéng)立的前提下,第44.1條可以不進(jìn)行實體審理。但在實踐中,關于第44.1條與其他條款并用問題,司法判決則呈現出明顯的多樣(yàng)性或者說不一緻性,有的直接對(duì)第44.1條不予評述,有的則進(jìn)行了實體審理但結論爲不成(chéng)立,這(zhè)兩(liǎng)種(zhǒng)做法本質上是矛盾的。除此之外,還(hái)有以下幾種(zhǒng)做法特别值得注意。
情形一:當事(shì)人的在先權利已得到保護,故不再适用第44.1條。例如在第9767386号“JIPU”商标無效案[1]和第16693707号“雷爾夫歐派”無效案[2]中,一審判決不再适用第44.1條的理由爲:原告的在先權利已分别通過(guò)第13條和第30條予以保護,故不再适用第44.1條。在第11059128号“藍美蘇”商标無效案[3]中,一審判決的評述則更近了一步,該判決指出訴争商标注冊人申請注冊與原告及其他知名白酒品牌相近似的商标屬于損害特定民事(shì)權益情形,鑒于已适用2001年商标法第28、29條對(duì)原告的在先商标權予以保護,對(duì)其提出的第44.1條的主張不再予以支持。此種(zhǒng)裁判方式反映出兩(liǎng)個問題:其一,在先權利條款與第44.1條具有何種(zhǒng)聯系,爲什麼(me)當事(shì)人的在先權利得到保護就可以不再适用第44.1條,這(zhè)樣(yàng)做是否合乎法律适用邏輯?其二,將(jiāng)大量仿襲型注冊認定爲損害特定民事(shì)權益有違一貫的行政和司法審查實踐,而且,多個損害特定民事(shì)主體利益事(shì)實的疊加是否有可能(néng)導緻申請注冊行爲的性質發(fā)生質變亦不乏探讨空間。
情形二:在其他條款成(chéng)立基礎上,認定其他不正當手段亦成(chéng)立,但參照前案不适用第44.1條。例如第12049178号“麥旋風”商标無效案[4]中,一審判決首先認定訴争商标的注冊違反了商标法第13條第3款的規定,然後(hòu)評述了訴争商标注冊人及其唯一的股東注冊了多件與他人知名商标近似的商标,擾亂了商标注冊秩序,最後(hòu)鑒于已适用第13條保護,參照2015高行終字第659号判決精神,不再适用第44.1條。我們認爲這(zhè)種(zhǒng)裁判方式是在不違背高院審理指南17.5規定的前提下,對(duì)仿襲型注冊仍予以審理并做出實體性評價,屬于折衷式做法。好(hǎo)處是對(duì)類似注冊情形可以起(qǐ)到震懾作用并對(duì)申請注冊行爲給予正确的指引,不足之處仍在于法律适用邏輯存疑。
情形三:在認定第44.1條成(chéng)立的基礎上,不再評述第13條馳名主張。在第9594513号“伊卡璐”商标無效案[5]中,一審判決首先認定第44.1條以其他不正當手段取得注冊成(chéng)立,繼而對(duì)當事(shì)人依第13條提出的主張不再評述。這(zhè)種(zhǒng)做法同樣(yàng)面(miàn)臨法律适用邏輯的拷問,同時與第一種(zhǒng)情形展現出的法律适用态度完全相反,不免令人疑惑:其他實體條款和第44.1條在适用上究竟孰先孰後(hòu)?
情形四:在其他條款成(chéng)立的基礎上,同時适用第44.1條。在第11194669号圖形商标無效案[6]中,一審判決認定訴争商标的注冊既損害了他人在先著作權,同時構成(chéng)44.1所指的以不正當手段取得注冊之情形。在10719314号“鑒郎醇”商标無效案[7]中,一審判決認定訴争商标的注冊同時違反了商标法第19.4條和第44.1條的規定。在第21682535号“吃不忘老鵝”無效案[8]中,一審判決認定訴争商标的注冊同時構成(chéng)第32條損害他人在先商号權、搶注他人已經(jīng)使用并有一定影響商标以及第44.1條以其他不正當手段取得注冊的情形。在第12347780号“JIOPPLECHENG”商标無效案[9]中,一審判決認定第13條和第44.1條同時成(chéng)立。在第12138854号“美中宜和及圖”商标無效案[10]中,一審判決突破區分表适用第30條,在此基礎上繼續認定第44.1條成(chéng)立。在第四種(zhǒng)情形中,第44.1條與多種(zhǒng)實體條款和諧共存了,這(zhè)與第一種(zhǒng)情形所呈現的法律适用态度截然相反。
我們認爲,以上的法律适用矛盾主要源于對(duì)第44.1條的性質與功能(néng)認識不清,從而錯誤理解了該條款與其他實體條款的關系。
第一,第44.1條屬于絕對(duì)事(shì)由條款,與相對(duì)事(shì)由條款在适用上不存在互斥性。
首先,從第44.1條所處位置以及不受5年時間限制這(zhè)一點來看,該條款的性質毫無疑問屬于絕對(duì)事(shì)由。在當事(shì)人同時主張絕對(duì)事(shì)由和相對(duì)事(shì)由的前提下,相對(duì)事(shì)由的成(chéng)立不應影響絕對(duì)事(shì)由的審理。這(zhè)是因爲:其一,商标标識本身可能(néng)同時構成(chéng)相對(duì)事(shì)由和絕對(duì)事(shì)由所指情形,類似于駁回複審案件中要全面(miàn)審查相對(duì)事(shì)由和絕對(duì)事(shì)由,不予注冊複審或無效宣告案件中也應當在依申請原則下對(duì)系争商标的可注冊性進(jìn)行全面(miàn)審查,這(zhè)樣(yàng)才能(néng)保持整個商标授權确權程序中法律适用标準的一緻性。尤其是所謂的其他實體條款既包括第30條、第32條等相對(duì)事(shì)由條款,也包括第10條、第11條等絕對(duì)事(shì)由條款,司法實踐中對(duì)于當事(shì)人同時提出的以上絕對(duì)事(shì)由和相對(duì)事(shì)由主張都(dōu)會(huì)進(jìn)行審查,那麼(me)第44.1條作爲絕對(duì)事(shì)由之一種(zhǒng),有什麼(me)理由被(bèi)排除在審查範圍之外?其二,法律事(shì)實認定的複雜性決定了在不違背依申請原則的前提下,相對(duì)事(shì)由和絕對(duì)事(shì)由均應納入審理範圍,否則可能(néng)會(huì)造成(chéng)商标授權确權效率的下降。例如在第13431834号“Go Pro”商标無效案[11]中,評審部門在認定商标法第31條成(chéng)立的情況下對(duì)第44.1條未予評述,進(jìn)入司法程序後(hòu),一審判決認定商品不類似故第31條不成(chéng)立,評審部門應對(duì)第44.1條進(jìn)行評述。類似的情形還(hái)可能(néng)發(fā)生在一審和二審之間,二審和行政程序之間。允許同時适用就可以避免以上這(zhè)種(zhǒng)不必要的程序浪費。
其次,有觀點認爲大量或多次搶注他人商标,侵害的依然是特定人的利益,是侵害法益的行爲,多個“法益”的相加不會(huì)“質變”爲公共利益,故而仍屬相對(duì)事(shì)由[12]。前述“藍美蘇”案正是基于上述理論所做的裁判。我們認爲,多個私法益的簡單相加的确不會(huì)質變爲公共利益,但大量仿襲型搶注的情況絕非多個損害私法益情形的簡單相加,有的情形甚至并不構成(chéng)對(duì)私法益的損害[13]。在大量仿襲型注冊中,注冊人的針對(duì)目标系不特定主體,這(zhè)與針對(duì)特定主體的搶注情形有所不同,後(hòu)者對(duì)其他不相關權利人幾乎沒(méi)有影響,而前者的行爲如不及時制止,則會(huì)造成(chéng)注冊簿上多數權利人的恐慌,從而導緻盲目的防禦性注冊,嚴重虛耗了資源。此外,我國(guó)的商标申請費用低廉且不要求提供使用或意圖使用證據,由此導緻大量仿襲型注冊人濫用商标申請權,扭曲商标功能(néng),歪曲了商标注冊制度。這(zhè)種(zhǒng)搶注目标的不特定性以及結果的嚴重性,絕不是損害私益可以解釋的。
再次,對(duì)大量囤積型注冊、仿襲型注冊适用第44.1條予以規制在實踐中已達成(chéng)共識,且形成(chéng)了相對(duì)穩定的法秩序,2019年新修訂的商标法肯定了這(zhè)種(zhǒng)共識,并通過(guò)修改第4條使規制囤積型和仿襲型注冊的法律依據更加明确。第4條作爲絕對(duì)事(shì)由條款的性質不容置疑,與其内容相對(duì)應的第44.1條當然應具有相同的性質。如果當事(shì)人在不予注冊複審或無效宣告中同時援引了第4條和其他實體條款,根據現行法律規定和法律适用規則,無論是行政機關還(hái)是司法機關,即使在其他實體條款成(chéng)立的情況下,恐怕都(dōu)不能(néng)回避第4條的審理。考慮到法不溯及既往原則,第4條和第44.1條在無效宣告案件中可能(néng)將(jiāng)長(cháng)期并存适用,如果第4條與其他實體條款可以并用,而規制同樣(yàng)情形的第44.1條卻不能(néng)并用,法律适用标準的統一性將(jiāng)受到破壞。
第二,第44.1條與其他實體條款并非一般與特殊的關系,其他實體條款因此并不具有适用上的優先性。
這(zhè)是因爲:其一,第44.1條作爲絕對(duì)事(shì)由之一種(zhǒng),與其他相對(duì)事(shì)由條款之間不存在一般與特殊的關系,因此,其他相對(duì)事(shì)由條款與第44.1條相比,并不具備适用上的優先性。其二,第44.1條作爲絕對(duì)事(shì)由條款,與其他絕對(duì)事(shì)由條款(如第10條、第11條等)之間同樣(yàng)不構成(chéng)一般與特殊的關系,因爲第44.1條的立法用語是“其他不正當手段”,這(zhè)裡(lǐ)的“不正當手段”與前述的第10條、第11條等完全不具備包含關系,這(zhè)一點與商标法第11.1條中的包含性兜底條款設計有所不同[14]。由此,其他絕對(duì)事(shì)由條款與第44.1條相比,亦不存在适用上的優先性。
小結:通過(guò)對(duì)第44.1條在司法實踐中的适用情況進(jìn)行梳理和分析,我們認爲該條款與其他實體條款在适用上并無先後(hòu)之分,對(duì)當事(shì)人提出的相關主張,裁判機關應予以一并審理。高院審理指南17.5規定以及司法實踐中拒絕同時适用的做法在理論上難以自圓其說,不僅會(huì)造成(chéng)後(hòu)續法律适用上的矛盾,而且不利于維護業已形成(chéng)的穩定的法秩序,進(jìn)而有損于當事(shì)人的信賴利益和司法審判的權威性。
二、關于超5年時間限制适用第13條的問題
在分析整理2018年敗訴判決過(guò)程中,我們發(fā)現超5年無效宣告案件在司法程序中得到了較多支持,這(zhè)與評審部門一貫的審理實踐明顯不一緻,有必要展開(kāi)進(jìn)一步探讨。
商标法第45條第1款明确規定對(duì)違反本法第13條第2、3款的已注冊商标提起(qǐ)無效宣告的,應在商标注冊之日起(qǐ)5年内提出。但該條随後(hòu)又規定了例外情形:對(duì)惡意注冊的,馳名商标所有人不受5年時間限制。實踐中,造成(chéng)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分歧的關鍵就在于如何界定第45.1條所指的 “惡意注冊”。行政機關認爲,此處的惡意注冊系指“複制、摹仿、翻譯”之外的其他惡意情形,而司法機關則基本上將(jiāng)“複制、摹仿、翻譯”本身等同于例外規定中的“惡意注冊”。
在第7264299号“LOUIS CADENS及圖”商标無效案[15]中,訴争商标于2010年8月28日獲準注冊,無效宣告申請時間爲2016年5月30日,被(bèi)訴裁定以超5年且未能(néng)證明馳名及惡意注冊爲由,對(duì)無效申請人主張不予支持。一審法院認爲在引證商标、已爲相關公衆廣爲知曉情況下,應推定訴争商标原注冊人明知引證商标的存在,但其仍使用“LOUIS”作爲商标主要識别部分,不能(néng)排除主觀上具有搭便車的故意,故本案不受5年時間限制。此外,在雙方商标核定使用商品相同的情況下,該一審判決認定原告(無效申請人)基于2001年商标法第28條和第13條提出的主張均成(chéng)立,并據此撤銷了被(bèi)訴裁定。
在第1475893商标無效案[16]中,一審判決認爲,引證商标爲臆造商标且在訴争商标申請日前已達馳名程度,訴争商标申請人經(jīng)營廣告業務,理應知曉引證商标,且無證據表明其選擇“奧普”商标具有正當理由。綜上,可以推定訴争商标構成(chéng)第45.1條所指的“惡意注冊”情形。
在第3709504号商标無效案[17]中,一審判決認爲,訴争商标與引證商标圖形花瓣數目相同,整體設計風格相近,構成(chéng)複制摹仿;原告與第三人之間曾簽署侵權解決協議(非針對(duì)本案訴争商标),第三人在知曉引證商标知名度的前提下,應主動避讓近似商标的申請注冊,但其仍申請注冊訴争商标,具有惡意。
在這(zhè)些超5年獲得支持的案件中[18],法院基本上將(jiāng)“明知或應知”等同于第45.1條所指的“惡意注冊”,從而認定無效申請人的主張不受5年時間限制。但實際上,這(zhè)裡(lǐ)的惡意不過(guò)是“明知”而已。而商标法第13條中“複制、摹仿、翻譯”的立法用語本身已經(jīng)隐含了“明知”要件,如果將(jiāng)“明知”等同于“惡意注冊”,意味著(zhe)對(duì)所有違反第13條的注冊商标提起(qǐ)無效宣告均不應受5年時間限制。這(zhè)種(zhǒng)解釋方法將(jiāng)使第45.1條出現自相矛盾,形成(chéng)法律漏洞,無論從解釋的路徑還(hái)是效果來看,都(dōu)不是明智之選。最佳解釋方法應以第13條的文義解釋爲錨,對(duì)第45.1條中的“惡意注冊”進(jìn)行目的性限縮。這(zhè)種(zhǒng)解釋方法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合理性體現在:
第一,從法律解釋規則的層面(miàn),文義解釋在順序上當然具有優先性,與作爲不确定法律概念的“惡意注冊”相比,“複制、摹仿、翻譯”這(zhè)組動詞的含義簡直無法作他解。同時,在确認商标法第13條已包含“明知或應知”要件的基礎上,對(duì)第45.1條中的“惡意注冊”進(jìn)行目的性限縮,有利于消除法律規定本身的沖突與矛盾,這(zhè)種(zhǒng)解釋也符合法教義學(xué)的要求。
第二,從概念層面(miàn),“惡意注冊”是商标法上的特有稱謂,與僅指代應知或明知狀态的“惡意”相比,其内涵更加豐富。誠然,明知或應知意義上的“惡意”作爲常用法律詞彙,可能(néng)影響了我們對(duì)商标法上惡意注冊的理解,但實際上,僅有“明知或應知”要素,不足以成(chéng)立“惡意注冊”。從“惡意注冊”對(duì)應的英文稱謂bad faith filing來看,其實質應爲非誠信注冊,具體表現爲注冊人違背誠信原則所爲的注冊,在主觀方面(miàn),除明知或者應知外,尚需滿足不正當目的或者權利濫用等表征。也就是說,惡意注冊所表現出來的主觀惡性更加嚴重,是比“明知或應知”更加惡劣的情形。但在跨語言交流過(guò)程中,中國(guó)商标業界基于對(duì)“惡意”一詞的熟識僅僅接受了bad faith filing中的“明知或應知”要素,而忽略了其他要素,由此導緻bad faith filing被(bèi)轉譯成(chéng)了“惡意注冊”。所以,應將(jiāng)“惡意注冊”作爲“非誠信注冊”的同義詞去理解,切不可將(jiāng)其簡單將(jiāng)等同于“明知或應知”情形下的注冊。
第三,從利益衡量角度來看,商标法已經(jīng)對(duì)馳名商标提供了比普通注冊商标力度更大的保護,所以在設定5年無效宣告時間限制時,立法者原則上將(jiāng)第13條與其他相對(duì)事(shì)由條款一視同仁,隻有在滿足惡意注冊情形下,才給予馳名商标權利人超5年的保護。如果僅僅因爲注冊人知曉他人在先馳名商标就可以提供超5年保護,對(duì)馳名商标的保護力度未免存在失衡之嫌。
第四,從正當行使權利的角度,馳名商标權利人在沒(méi)有正當理由的情況下,超過(guò)5年對(duì)已注冊商标提出無效宣告不僅有怠于行使權利之嫌,還(hái)會(huì)影響注冊秩序的穩定性,并可能(néng)對(duì)注冊人的信賴利益造成(chéng)損害。在第6338299号![]() 商标無效案中,一審判決認爲,訴争商标申請人明知“浪莎”商标的知名度,仍在類似商品上申請注冊訴争商标具有明顯攀附原告市場聲譽的意圖,該申請人曾于2004年申請注冊“浪莎新秀”及多枚含有“浪沙”的商标,進(jìn)一步佐證其惡意。第三人雖提交了使用證據及榮譽證書等,但在訴争商标申請注冊損害他人合法權益的情形下,前述使用情況不能(néng)成(chéng)爲維持注冊的理由[19]。值得我們關注的是,本案訴争商标注冊人的“明知或應知”情形發(fā)生在注冊伊始,浪莎公司本有機會(huì)迅速解決問題,但其放任同行業經(jīng)營者在相同或類似商品上長(cháng)期大量使用與其馳名商标相近似的訴争商标,直至訴争商标具有一定知名度[20]時才姗姗來遲地提起(qǐ)無效宣告,在缺乏正當理由的情況下,其怠于行使權利的行爲不應得到鼓勵,尤其是這(zhè)種(zhǒng)鼓勵導緻了訴争商标注冊人僅因“明知或應知”就永久喪失了豁免權,不僅如此,其在5年豁免期後(hòu)的信賴利益也被(bèi)裁判者徹底忽視了。如果法律适用的後(hòu)果會(huì)造成(chéng)這(zhè)種(zhǒng)利益失衡的狀态,裁判者有必要重新檢視法律适用标準,并對(duì)其進(jìn)行必要的調整。
商标無效案中,一審判決認爲,訴争商标申請人明知“浪莎”商标的知名度,仍在類似商品上申請注冊訴争商标具有明顯攀附原告市場聲譽的意圖,該申請人曾于2004年申請注冊“浪莎新秀”及多枚含有“浪沙”的商标,進(jìn)一步佐證其惡意。第三人雖提交了使用證據及榮譽證書等,但在訴争商标申請注冊損害他人合法權益的情形下,前述使用情況不能(néng)成(chéng)爲維持注冊的理由[19]。值得我們關注的是,本案訴争商标注冊人的“明知或應知”情形發(fā)生在注冊伊始,浪莎公司本有機會(huì)迅速解決問題,但其放任同行業經(jīng)營者在相同或類似商品上長(cháng)期大量使用與其馳名商标相近似的訴争商标,直至訴争商标具有一定知名度[20]時才姗姗來遲地提起(qǐ)無效宣告,在缺乏正當理由的情況下,其怠于行使權利的行爲不應得到鼓勵,尤其是這(zhè)種(zhǒng)鼓勵導緻了訴争商标注冊人僅因“明知或應知”就永久喪失了豁免權,不僅如此,其在5年豁免期後(hòu)的信賴利益也被(bèi)裁判者徹底忽視了。如果法律适用的後(hòu)果會(huì)造成(chéng)這(zhè)種(zhǒng)利益失衡的狀态,裁判者有必要重新檢視法律适用标準,并對(duì)其進(jìn)行必要的調整。
小結:商标法第13條的立法語言已經(jīng)表明了“明知或應知”要件,爲了防止出現法律漏洞,第45.1條中的“惡意注冊”應作限縮解釋,即除“明知或應知”之外,尚需滿足不正當目的或權利濫用之要件。此處的不正當目的或權利濫用可能(néng)表現爲:索要高額轉讓費、脅迫合作、在實際使用中誤導消費者、以不當方式妨礙真正權利人正常經(jīng)營(如自己不用,也不允許真正權利人用),其他表現可視具體案情進(jìn)行判斷,隻要訴争商标注冊人的客觀行爲能(néng)夠證明其主觀上具有超出“明知或應知”的惡性,均可以認定構成(chéng)第45.1條所指的“惡意注冊”。
(撰稿人:孫明娟)
[1] 一審案号2016京73行初5429号。
[2] 一審案号2019京73行初2148号。
[3] 一審案号2017京73行初9077号。
[4] 一審案号2017京73行初8742号。
[5] 一審案号2016京73行初2485号。
[6] 一審案号2017京73行初6967号。
[7] 一審案号2017京73行初4039号。
[8] 一審案号2019京73行初6554号。
[9] 一審案号2017京73行初3621号。
[10] 一審案号2017京73行初435号,本案二審判決已出,對(duì)一審判決予以維持,案号2019京行終3652号。
[11] 一審案号2018京73行初481号。
[12] 詳見李琛《論商标禁止注冊事(shì)由概括性條款的解釋沖突》,載于《知識産權》雜志2015年第8期。
[13] 因立法者的利益平衡考量,有些私益并未被(bèi)賦予權利的表征,亦難以構成(chéng)法益,從而無法得到法律的保護。例如被(bèi)搶注的商标可能(néng)僅具有地方性知名度或域外知名度,但在我國(guó)并未達到馳名程度,真正權利人又未在相同或類似商品上進(jìn)行過(guò)注冊或使用,則此種(zhǒng)情況下關于在先權利或法益受損的主張難以得到法律支持。
[14] 第11.1.3條“其他缺乏顯著特征的”中的“缺乏顯著特征”與前兩(liǎng)項明顯具有包含關系,因此構成(chéng)顯著性上的一般條款與特殊條款,在适用時應遵循特殊優于一般的原則
[15] 一審案号2017京73行初3723号。
[16] 詳見 2016京73行初3939号/2019京行終3972号,二審判決未就 “惡意注冊”作出明确評述。
[17] 詳見2016京73行初4885号。
[18] 類似案件還(hái)有很多,受篇幅所限無法一一具體闡述,筆者將(jiāng)收集到的部分案件案号予以列明,供讀者自行查閱。2016京73行初4886号櫻花圖形案、2018京73行初10652号“中信TN及圖”案、2017京73行初3153号“九牧王及圖”案、2017京73行初6316号“迪麗蒙”案、2018京73行初6308号“Hankook”案、2016京73行初6802号“天地上工”案、2018京73行初7514号“恒适”案、2018京73行初3689号“FSCHRB及圖”案等。
[19] 詳見2016京73行初6166号/2019京行終3673号。
[20] 訴争商标産品2013年獲評“河北省中小企業名牌産品”,訴争商标2016年被(bèi)認定爲河北省著名商标。
掃二維碼用手機看